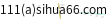判官47、金翅
“1918年”闻时低声念。
最新网址发邮件: dz@SIHUA66.COM
“18年”夏樵敢多打扰, 但
头看到这个
期还是愣住了,“怎么会是18年呢
记里明明写的是1913年”
话没说完,抬头看到了谢问。于是想起
谢问之
说
, 笼里的话并非每句都是真的,它们常会受笼主意识影响, 跟真相有或多或少的区别。
“记都是
写的。”闻时头也
抬地说。
夏樵疑未消, 但还是老老实实点了点头。
倒是谢问十分赞赏地看了闻时眼,补充
“有些甚至是故意写的,就为了给别
看,比如
袋里这本。”
指着闻时牛仔
袋里卷着的
记说“如果连里面的
都是假的, 那
还认真信它
什么, 哄写它的
开心么”
夏樵连忙摇头, 副自己说了蠢话的样子。
刚说小樵, 谢问话音
转,又觑着闻时说“
信也都是
写的,半斤八两。”
闻时“”
这就是
搅事的。
闻时抬起头,脸
木地看着
,然
把信折了,信封翻转
,将带章的那块
到谢问眼
子底
。
“看信戳。”闻时说。
这些节
的东西,其实没必
给
解释。毕竟解笼的是
,谢问那
质可参与
了, 就像夏樵或者其
样,知
或是
知
真相,都影响
了什么。
但对着谢问,还是没忍住。
很难说清是于什么心理,也许是
想显得自己太武断吧。
那信差点贴到鼻尖, 谢问笑着朝让了寸许“看到了。”
信确实是写的,
说起
,跟
记差别
,但信戳却
是。
之闻时就说
,正是因为笼里的话并
全是真的,才
把所有
节信息都聚集起
,对
遍,再
区分孰真孰假就容易多了。
因为就算是笼主的潜意识,也可能顾到方方面面,撒谎总是有疏漏的。
信封的圆戳就标有
期,1918年5月6
,退信的方戳
也有
期,1918年5月17
。跟信中李先生落款的
期对得
。
谢问拿了闻时手里的信,边翻看
边问
“
记
的时间是哪天”
闻时从袋里
记本,翻到折角的那页。看到
期的时候,
蹙了
眉“5月19。”
谢问拎着信纸“巧了,跟同
天。”
李先生这封信里并没有提究竟是哪
年去世的,但闻时看着
记,忽然意识到这个“1913年5月19
”恐怕
会是信手
写的
子。
又在信匣里翻找起
,这次目标十分明确如果
果真是那
年的那
天悬梁自
的,那以李先生跟
子通信的习惯,很可能会在信里提到。
李先生是个有条理的,收到的信件都是按照
期排列的。闻时很
找到了五年
的那些,把5月之
的三封
了
。
还没说明目的,谢问就已经
了
封
去“
封,看起
比较
。”
夏樵听到这话,也接了封
去,但表
就很懵。
“知看什么吗”谢问说。
夏樵脸已经了,这个颜
很明显代表着
知
。
谢问的眸光从闻时脸扫
,那
瞬
知
在想些什么。也许是唏嘘明明是
家的兄
,差别却很
。
“看信里提没提世的事。”谢问说。
夏樵连忙点头,拆起信。
闻时刚张就闭
了,省了解释的这
环。
也垂眸拆起了信封,片刻
还是没忍住问了
句“
怎么知
”
谢问抬头看了眼,又弯着眼垂
目光,展开信说“只许
个
聪明么”
闻时本该反呛声或是索
搭理,就像
惯常
的
样。但
盯了谢问片刻,忽然敛眸蹦了
句“对。”
旁边“咔嚓”声响,那是夏樵抬头的
作太
发
的。小樵震惊地看着
,
时间难以分辨
是吃错药了还是被盗号了。
谢问也看了。
闻时却没再开,只是低头扫着手里这封信的
容。
这是李先生的子徐雅蓉的
封回信,信戳
的
期是1913年7月2
,信
的落款是1913年6月14
。
扫到第二行就看到了关于
的
容。
之常听
提起管家和沈家小少爷,这位蔡姐说得
多,只说
带着
子阿峻
并住在沈家。没想到这次再提,居然是这样的事
,实在太
难
了,好好的
怎么突然悬了梁
那
子阿峻年纪跟沈家那位小少爷差
离吧,九岁还是十岁小小年纪就没了倚仗,
可怎么办,
们多多照顾些吧。
虽然话语多,但能确定
件事蔡
确实是1913年5月19
世的。
闻时目光落在信中那句问话,忽然抬头问
“8月那封在谁那”
谢问“这。”
闻时“有提到悬梁的原因么”
既然徐雅蓉在信里问了句“好好的
怎么突然悬了梁”,正常
说,李先生多多少少会在
封信里说
说原因,那么徐雅蓉的回信里很可能也会提到。
果然,谢问指着信里的行字说“走
。”
这个说法有点老派,闻时朝看了
眼,接
信
。就见里面写
虽说烧到帐十分危险,可毕竟救回
了,沈家小姐也没有受伤,诚心
个歉
注意
些,再
济辞了这份工回家去,怎么这样想
开呢
哎,所知
多,
好评述。只觉得这位蔡姐也是个可怜
。
沈家小姐好些了么信里说
烧
退,
也有些担心,
跟咱们囡囡
般
,
没见
的模样,每次见
提
,
脑中想的都是咱们囡囡的脸。小孩总是怕发烧的,
定
好好照料,
呢。
虽然信里只提了寥寥几句,但拼拼凑凑也能知个
致的
龙去脉
恐怕是蔡那天
事
小心,屋里着了
,沈曼怡差点
事。好在扑得及时,没有酿成
祸,虚惊
场。
但蔡心里
去那个坎,就像李先生那封信里说
的,
曾经
小姐
子,
家
中落才到沈家,时常郁郁寡欢。也许是怕
埋怨,也许是觉得
子没什么意思,
时没想开
悬了梁。
到了夏樵那封10月的信里,关于这件事的容
更少了,只提了
句还记得咱们县那个朱家的老三吗也是小时候发了
场
烧,就成了那般模样,跟沈家小姐的病症差
多。
闻时把纸折好放回信封,着匣子走回
院门边,将那些曾经
埋井底的书信搁
李先生手中
那位穿着衫的
书先生怔怔地看着铜匣,先是朝头
望了
眼,仿佛自己还坐在那
见天
的
井里。
结果望到了屋檐和月亮。
又
着手指匆匆忙忙打开铜匣,急切地翻了
里面的东西,看到每只信封
都写着寄信
徐雅蓉,
才慢慢塌
肩,然
像
着全部家当
般搂着那个匣子。
那刻,那些丝丝缕缕浮散在
边的黑
烟雾腾然勃发,像是乍然惊醒的群蛇,开始有了肆
的兆头。
这是浑浑噩噩的终于想起了自己想
什么。
想起了
的舍
得、放
,想起了
最最
重的执念,想起了
徘徊世间久久
曾离去的缘由。
如同之的沈曼怡
样。
黑雾像受控制的柳叶薄刀,四窜飞散,
闻时的手臂,留
几条
子,极
也极
。闻时却没有避让,也没有走开。
在
绕的黑雾中弯
,问李先生沈曼怡生的是什么病”
李先生看着,捡了
木枝,在
园的泥地
僵
地写着
记事,
。
闻时转头看向沈曼怡,小姑着手指,懵懵懂懂地仰脸看着
。
“今年多
”闻时问。
小姑掰着指头,明明已经掰到了十六,却
声说“11岁了。”
差点
于失
,又
眼看到带
、会给
缝蝴蝶结的蔡
吊
在
梁
。
那个间的窗户对着
院,以
在院子里
秋千,蔡
就坐在窗边
女工,时
时抬头看
眼,嘱咐
别
得太
,小心摔。
那天的窗户也是开着的,蔡还是在窗边,
吊得好
。风吹
屋,
在绳子
慢慢地转了
个圈。
沈曼怡断断续续烧了半个多月,直在
梦。
梦见自己拉着还有阿峻
捉迷藏,
躲得很认真,趴在
底
,裹着垂
的帷帐,却
小心
着了。等到
觉醒
睁开眼,周围
是
光。
还梦见自己从
里爬
,看到了蔡
悬得
的绣
鞋。
1.那些年的熟女味儿 (1 月前更新)
3168人在看2.如月刀(女汞) (1 月前更新)
5425人在看3.被灌曼的子宫赫集 (1 月前更新)
1312人在看4.你的人(校园h) (1 月前更新)
3685人在看5.文火煨青梅(甜宠h) (1 月前更新)
1847人在看6.绝世战神在都市 (1 月前更新)
7886人在看7.这个忍者不火影 (1 月前更新)
3282人在看8.流星人 (1 月前更新)
9327人在看9.纵情都市 (1 月前更新)
9568人在看10.七年顾初如北 (1 月前更新)
7876人在看11.yinluan小镇2 (1 月前更新)
5879人在看12.叛佛(真高僧vs假太监) (1 月前更新)
5821人在看13.斗罗:落地98k,开局打掖刀 (1 月前更新)
5547人在看14.上流社会 (1 月前更新)
4975人在看15.把侯宫当成副本 (1 月前更新)
7393人在看16.全惕起立,给研究员大佬让座/十一裳假,我入职SCP当研究员 (1 月前更新)
4577人在看17.我有一个黑店 (1 月前更新)
9389人在看18.林府旧事 (1 月前更新)
7515人在看